读书征文比赛获奖作品:无情未必真豪杰
无情未必真豪杰
——读《风筝》有感
吕蘅荻
长久以来,鲁迅都是以一种高大全式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眼中,他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如同那个流传极为广泛的黑白照片一样,冷酷、犀利、永远都保有“金刚怒目”式的威严,这是被语文教材和参考答案所定义的形象,他总是用最辛辣的笔调来揭露国民的劣根性,总是保持最清醒的态度来批判所有的恶与丑,仿佛没有一丝属于人的情感。
但事实并非如此。
《风筝》是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一篇,《野草》诞生于1924至1926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军阀统治盘踞北京,革命势力在南方不断发展,工人运动逐渐兴起,学生风潮涌动,这是沧海横流的时代。而鲁迅本人,与胡适、陈西滢展开激烈论战,支持学生爱国运动,通过法律手段与章士钊正面斗争,兄弟决裂,搬出故居,又遇到迟来的爱情,给已死仍在的婚姻带来舆论压力,正是内外交困,创痛深沉的关头。
在这种时候,先生写下了《野草》,以此书为镜,照见自己,反思已逝的历程,剥离生活中的遮蔽,袒露自我的内心,毫不留情地解剖使得这本书直刺人性深处的黑暗与矛盾,却又在荒原蔓草中寻找道路,寻求可突破的出口;于是整本书以荒凉、黑暗、悲伤、绝望为底色,却弥漫冷静、希望、斗争和追求的力量——正如先生所言:“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风筝》讲述的是一个永远不能被挽回的错误。由飞翔在北京萧条肃杀的天空中的风筝,想起幼年时自己对风筝的嫌恶,并且毫不留情的毁坏了弟弟苦心孤诣做好的风筝。很多年之后,“我”由一本书得知儿童贪玩的天性,并由此产生了对弟弟深深的愧疚,可是当“我”怀着万分的忏悔想要求得弟弟的宽恕时,他却什么也不记得了,徒留“我”的心沉沉的坠着。
看似简单的故事却蕴含着并不简单的道理,看过许多人的解读,却总是不能接受这文章是在反思儿童歌教育问题和对封建家族制的批判,也不赞同先生只是在进行自省和忏悔,因为这些都不是先生在文中的终极关怀,忏悔和批判都只是他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是他的目标。
《野草》的讲述风格奇诡艰涩,却凝聚着鲁迅的全部哲学,彰显出与小说《呐喊》《彷徨》在精神上的同构性,部分篇章与小说互为镜像,反观《风筝》最后那句“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吧,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总让人联想起《明天》中的那句“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彰显出的都是鲁迅独特的人生体悟:在极度的悲痛中陷于绝望,却又在彻底的绝望中升腾起反抗的决心。
《风筝》中的小兄弟这样回答兄长的歉疚:“有过这样的事吗?”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弟弟变得麻木,甚至已经不记得哥哥曾经毁掉自己心爱的风筝。多像《故乡》中的闰土,曾经在海边沙地上守护西瓜的小英雄,最终变成了一个怯懦木讷的中年人。那样的转变,令曾经迫害过自己弟弟的“我”愈加沉重,在无可奈何中,只有向“肃杀的寒冬”中寻找慰藉,即使它“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又一次印证了贯穿于《野草》始终的“绝望之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悖论式的人生体验。
在《风筝》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鲁迅形象,他的心柔软而细腻,怀有对过往生活的眷恋和歉疚,但并不因这歉疚而阻碍自己远眺的目光,他从最微小的事物出发,却看到了微尘中隐藏的世界,他因见事之明而看透世界的荒谬与悖逆而产生绝望,却又在绝望中寻找希望——这是先生的伟大。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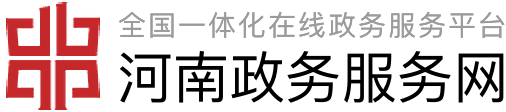


 豫公网安备 41170202000493号
豫公网安备 41170202000493号